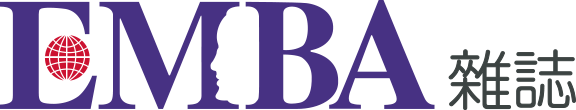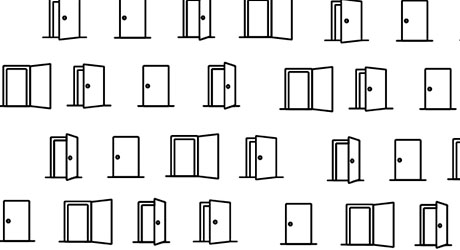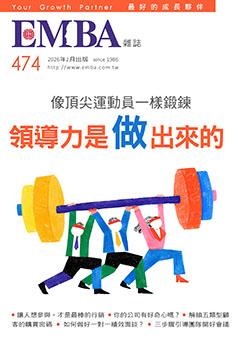成為不確定時代的贏家

當突如其來的政治變動,讓許多企業成本上升,策略失靈,企業必須重新思考自己與政治互動的方式。向利樂公司、巴菲特等跨國企業與領導人,學習感知弱訊號,提升政治風險的準備力。
當企業正在思考生成式AI的未來、面對能源稀缺、成本上漲的挑戰時,有一股更難預測的力量,正衝擊著企業的種種決策:政治變動風險。
自疫情爆發以來,全球企業早已歷經連番震盪。從俄烏戰爭、中東衝突,到二○二五年美國總統大選等接連不斷的政治變動,讓許多企業的策略幾乎無法穩定落地。
根據BCG顧問公司一項涵蓋近七千家企業、橫跨二十年的研究分析顯示,企業獲利表現的差異,已有高達四三%來自「情境因素」(contextual factors),包括地緣政治、科技突破,以及氣候變遷等,這些都遠超過企業內部或產業本身的影響力。
BCG亨德森研究所策略實驗室領導人賈伯(Adam Job)提醒,特別是政治變動,已成為今天最不可忽視的變數,政治風險不再只是地圖角落的備註,而是主戰場的一部分。高階主管若無法正視其特性與影響,就會在突如其來的浪潮中措手不及;企業若未將「政治風險」納入策略設計,將難以建立真正的韌性與前瞻。
重新思考企業與政治的互動方式,才能讓企業在風險中穩健前行。賈伯等顧問在史隆管理評論(Sloan Management Review)中,提出一套協助企業應對政策變動挑戰的做法:
第一階段:感知政治風險
1. 利樂公司
觀察政治地貌,讓資訊進入決策
若要有效制定政治風險策略,企業領導人必須先接受一個事實:只關注公司本身,以及其市場環境已經不夠了。
企業需要建立偵測政策趨勢的能力,例如定期與相關政治人士互動、參與政治論壇,或是隨團出訪。加入產業聯盟也是一種務實做法,這些聯盟可協助成員公司追蹤相關法規,並促成與政治決策者的交流。
在掌握重要政治動態的基礎上,企業可以進一步追蹤相關的關鍵績效指標(KPI),以便及早察覺某些議題正在升溫。例如,歐洲食品加工與包裝巨擘利樂公司( Tetra Pak ),就追蹤並解讀超過四十項全球指標,涵蓋包裝與廢棄物法規、回收基礎建設投資等項目。
更進一步,企業也可以主動蒐集與分析「弱訊號」(weak signals),以預測可能出現的新政策,舉例來說,可以藉由了解大眾在相關議題上的情緒與觀點,來研判政策走向。麻省理工學院與微軟的研究人員就曾指出,社群媒體上的互動數據,可以高度準確地預測政策變動的結果。
2. 汽車製造公司
發展情境推演,預演未來政治路徑
預測不等於預知未來,而是準備好面對多種可能的狀況。為了因應政治決策可能帶來的衝擊,企業必須以情境思維來進行準備。透過延伸現有政治趨勢,或將多個趨勢結合,甚至如世界經濟論壇所建議,從科幻作品中描繪的另類未來獲得靈感。策略規劃人員可以描繪出各種可能的未來政治局勢,進而更清楚理解潛在的機會與風險。
一旦描繪出與企業高度相關的一組情境,策略團隊就能進一步辨識與這些情境相對應的「預警指標」,也就是那些顯示某一情境逐漸成為現實,並且與之相關的能力需求正在上升的徵兆。
例如,汽車製造公司預測一種未來情境是:「某國會在明年實施更嚴格的碳排法規」。因此開始觀察一些「預警指標」,像是:該國環保部門近期是否公開談論相關法案?是否出現公眾輿論對碳排放加強監管的呼聲?是否出現政治人物在選舉中將此議題列為政見?
如果發現這些指標開始同時出現或頻率增加,就代表這個情境可能成真,公司要接著採取行動,像是開始盤點自身碳排量、加快開發電動車、調整行銷策略等等。
進行情境思考不僅需要具備延伸、組合與分析關鍵趨勢的專業能力,同樣重要的是,企業領導人也必須願意跳脫現有的世界觀與思維模式,真誠面對那些看似不可能,卻可能帶來重大影響的未來局勢。
3. 波克夏海瑟威公司
精選戰場,設定合理參與邊界
不是所有政治議題都值得企業介入。 公司應聚焦在與自身核心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政治議題,這樣的介入才具正當性,也讓企業能以專業角色參與討論。例如,汽車製造商就應該在車輛安全規範或排放標準等議題上發聲。
近年來,企業面臨來自利害關係人日益強烈的壓力,被要求「表態」或「發聲」。要減緩這類壓力,企業也應明確定義「機構中立」的立場。舉例來說,自一九六七年起,芝加哥大學就明確表態:「學校應作為批判者的家與支持者,而非批判者本身。」
這一立場讓芝加哥大學在面對近期政治議題時,比其他學術機構更能穩健應對。例如,在美國各地校園近期針對中東戰爭的抗議活動中,芝加哥大學雖也有相關聲音,但並未因此出現高層請辭,或學校領導人被傳喚作證的情況。
波克夏海瑟威公司(Berkshire Hathaway)也採取類似做法,其執行長巴菲特(Warren Buffet)雖然經常對政治議題直言不諱,但公司從不介入社會運動,他堅持不以公司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工具,反而維持了品牌的一致性與長期信任。
本文未完,全文請見EMBA雜誌465期